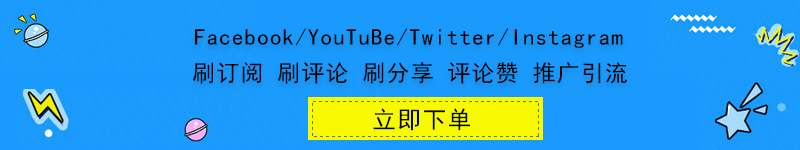我的故乡回忆
福建泉州的小岞岛,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那是个小渔村,嵌在90年代初的海风里,日子简单得像海滩上的沙子,一粒一粒,清清楚楚。村子不大,百来户人家,里里外外都是宗亲,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炖了鱼汤,香味飘出去,半个村子都能闻着味儿找过来。海就在村子里,潮起潮落,像村里的钟,准时地响着,提醒着我们这些靠海吃海的人,日子得跟着海走。
我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家里没田地,也没农耕,贫瘠的石头地长不出庄稼,祖祖辈辈就指着海吃饭。父亲是个黑瘦的汉子,常年带着渔网出海,天不亮就走,月亮挂上树梢才回来。母亲守着家,操持着我和弟弟妹妹几个留守的孩子。大人忙,顾不上我们,我们便成群结队地撒野,赤脚踩在沙滩上,跑起来啪啪响,像海浪拍岸的声音。沙子烫脚的时候,就一头扎进海里,扑腾几下,水花四溅,笑声传出去老远。
村里的学校是个小院子,破旧得像风吹一吹就会散架。教室是几间低矮的平房,每个年级一个班,学生加起来也没多少。操场是片沙地,风一吹就扬尘,下雨就成泥坑。课间十分钟,老师一转身,我们就溜出去,偷偷跑到海边摸海螺。那时候没啥玩具,海就是我们的乐园。海螺藏在石头缝里,手一伸进去,凉凉的海水裹着指头,摸到一个硬邦邦的小东西,心里就乐开了花。拿回家,母亲用海水煮一煮,撒点盐,就是一顿鲜美的下饭菜。
教室后窗就是我家,隔着一堵矮墙,老师站在讲台上吼一嗓子:“陈阿婆,你家小石头又偷跑出去啦!”我娘准放下手里的活计,踩着拖鞋过来,揪着我耳朵往回走。村里就这样,谁家孩子犯了错,老师不用费神找家长,扯开嗓子喊一声,家长就到了。整个村子都是宗亲,几百号人左不过同宗同族的亲戚,谁跟谁都沾点血缘,吵归吵,闹归闹,遇事还是齐心。
日子清苦,但也有暖意。家里没啥值钱东西,桌椅是父亲用木板钉的,床是竹子搭的,咯吱咯吱响。晚上,母亲坐在门口补渔网,昏黄的煤油灯晃着光,海风吹进来,带着咸味。她不爱说话,手却没停过,指头粗糙得像老树皮。父亲回来,卸下鱼篓,里头有时是几条小鱼,有时是空的。他拍拍手,笑笑说:“海今儿不给面子,明儿再试试。”我们围着桌子吃饭,饭碗里是番薯粥,配上点咸鱼干,嚼得满嘴香。
那时候的回忆,总离不开海。清早,海面平得像镜子,渔船一艘艘出去,拖着长长的影子。中午,太阳毒,晒得沙滩发烫,海水却还是凉的,我们跳进去,抓小鱼,捡贝壳,玩得不亦乐乎。傍晚,海风大了,浪头拍着礁石,远远看去,像村子在喘气。夜里,海安静下来,只剩潮声,一下一下,像摇篮曲,把我们哄睡。
村里没啥娱乐,逢年过节才热闹。春节时,家家户户贴红纸,门口挂鱼干,祈求来年鱼多。端午包粽子,用的不是糯米,是番薯粉,硬邦邦的,吃不出啥甜味,可我们照样抢着吃。村里还有个老祠堂,逢大事就在那儿聚,宗亲们坐一块儿,商量着谁家渔船坏了要修,谁家孩子要上学缺钱。都是亲戚,没人计较太多。
学校里教的东西简单,语文数学加点唱歌画画。老师是个外乡人,说话带点硬邦邦的口音,可对我们挺好。他知道我们皮,课间跑出去也不真生气,就是敲敲桌子说:“下次再跑,抄课文十遍。”可我们哪管这个,铃声一响,又一窝蜂往海边冲。教室的窗户老旧,风吹进来,夹着海腥味,课本上写的字我记不住,满脑子都是海螺的模样。
那时候的我,觉得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海里有鱼,家里有饭,村里有亲人,啥都不缺。可慢慢地,村子变了。90年代末,外头的人开始出去打工,村里年轻人少了,渔船也少了。父亲说,海里的鱼不如从前多了,风浪也大了些。我长大了,离开小岞岛,去了城里读书,再后来工作,回家的次数少了。
如今想来,那些赤脚跑在沙滩上的日子,那些课间偷溜去海边的光景,都成了心里的宝。海还在那儿,村子还在那儿,可味道不一样了。母亲老了,手抖得补不了网,父亲也不出海了,坐在门口晒太阳。弟弟妹妹散在各地,逢年过节才能聚一回。宗亲们还在,可孩子们不认得彼此了,祠堂也冷清了。
小岞岛还是那个小岞岛,海依然绕着村子,可我再也摸不到当年的海螺了。那些贫瘠却温暖的日子,像潮水退去,留下一片沙滩,干干净净,又空落落的。每次回乡,站在海边,风吹过来,还是那个咸味,我闭上眼,像是又听见母亲喊我回家吃饭,老师在窗边吼我名字,赤脚踩沙的啪啪声又响起来。那是我的故乡,藏在90年代的海风里,永远也回不去的小渔村。
马斯克最新的Grok3的中文写作能力又有了大进步【起点吧】
用户评论 查看更多>>
相关服务
最新文章
-
深度干货:Facebook广告扩量的9个“硬核”方法
218阅读 -
独立站Facebook广告投放指南,5步实操策略助力出海引流
181阅读 -
企业出海必备:专业Facebook广告投放服务推荐
162阅读 -
海外短剧出海利器:如何通过Facebook广告投放打通流量入口?
179阅读 -
Facebook+独立站,原来还能这样玩!内附可复制出海案例!
187阅读 -
Facebook海外推广:品牌出海的关键抓手与策略解析
172阅读 -
APP出海如何在Facebook投放广告
183阅读 -
Facebook付费推广必看:广告形式与ROI提升指南
188阅读 -
二、精准定向:用 Facebook 工具锁定 “潜在游客”
181阅读 -
Facebook广告:最详细的Facebook广告投放攻略
176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