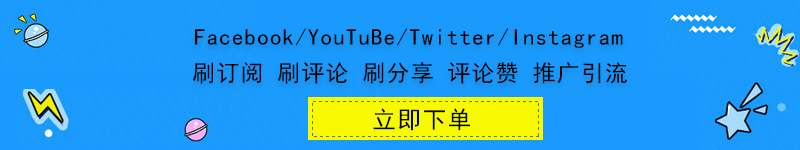当前国内平台领域的反垄断监管情况如何?未来可能呈现什么趋势?6月8日,南都第六期数字经济治理论坛以“反垄断:发展与规范并重,平台经济走向何方”为主题,邀请各界专家进行探讨。

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云、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仲春从数据竞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刘云认为,数据是平台经济中构成支配性地位或者“守门人”的关键,也是新型滥用行为的主要着力点,界定数据滥用行为是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工作的关键。仲春表示,数据可携带权的本质是保护用户个人数据和隐私,随着研究深入或立法推进,可以被考虑补充引入为竞争性执法工具。
数据垄断如何判定?有三个分析维度
刘云指出,数据是平台经济中构成支配性地位或者“守门人”的关键,平台拥有海量的用户数据使得其外部性效应大大扩张。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借助平台规则和技术措施的各种数据滥用行为层出不穷,界定数据滥用行为是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工作的关键。
那么,数据垄断行为该如何判定?他认为,重点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第一,平台与平台之间,是否存在滥用数据资源控制权而拒绝交易,或者滥用数据接口控制权而阻止正常的数据互通;第二,平台与用户之间,是否存在滥用用户个人数据从而构成剥削型滥用;第三,平台与商户之间,是否存在滥用商户数据进行不公平竞争。
刘云进一步解释,滥用数据接口控制权与滥用数据资源控制权是可以相互区分的两种行为。其中,平台对于自己创造的数据资源有权进行保护并做出商业决定,滥用数据资源控制权需要界定数据的基础性和“守门人”地位,这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的发展来共同推进规则的确定性。
但是,平台上的他人数据高度依赖平台数据接口进行互通。相比较而言,滥用数据接口控制权的行为应当优先作为反垄断规制的对象,因为平台作为多方数据的受托人,有必要保障他人数据权利的合法行使,从而促进数据在不同平台之间互通。此外,不提供数据接口往往是面向特定的开发者,这种行为很容易被认定为歧视性对待。
刘云梳理欧美的案例发现,近年来,欧洲立法方向是兼顾个人数据的可携带权和基础数据的公共属性,认为大型数据平台有义务保障数据的自由流通和可及性;美国通过司法裁判观点强调平台应保障公开信息自由获取,据此做出了一批鼓励数据自由流通的司法裁决。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应当避免生态之间的恶性竞争和互相诋毁,向着更加开放、互通的互联网发展。
刘云指出,用户个人数据滥用一般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但是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在2019年对脸书做出裁决成为将滥用他人数据拉入反垄断法规制的里程碑案件,该案指称脸书违反数据保护框架对用户的数据收集构成剥削性滥用。
《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指南》第17条将“大数据杀熟”列入差别待遇的滥用行为类型,也将为用户个人数据滥用适用反垄断规制打开一个窗口。不过刘云认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完善,个人数据滥用行为主要应当通过行政监管、民事救济得到处理,一般不能作为反垄断的独立事由,很难成为反垄断案件中作为消费者福利保护的考量因素。
数据可携带权本质是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
“数据流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仲春指出,当前已经出现互联网巨头利用数据制造出市场壁垒,排除、限制其他竞争者竞争的情况。为此,她提出了一种构想——未来随着研究深入或立法推进,数据可携权可考虑补充作为竞争执法工具。
所谓数据可携权,是赋予用户从现有数据控制者手中获取自己的数据,并携带到另一数据控制者的权利。从本质来看,数据可携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仲春认为,《欧盟数据保护条例》(GDPR)在设立这项权利的目标是赋予用户对个人数据更好的掌控力,但也同时注意到这对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影响。
南都记者发现,在欧美发起反垄断调查中,科技巨头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行为成为关注焦点。比如亚马逊在多个国家被质疑利用第三方卖家数据,实施偏袒自己产品和服务行为;谷歌则因诱导消费和扩大数据适用范围,而被澳大利亚执法机构“盯”上。
因此,在查处数据驱动型企业违法并购案,或规制巨头滥用垄断地位实施数据“作恶”行为,执法机构在协商中要求企业履行数据可携权,或许可成为竞争性执法的一种工具。
那么,如何判断某种数据是否属于数据可携权的范围?仲春认为,可考虑如下几个因素:该数据来源是否与用户个人直接相关;该数据是否影响市场准入门槛;该数据的迁移成本及产生的效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数据迁移是否会侵犯其他合法权益;迁移平台之间在数据保护层面能力是否较为接近。
仲春建议,设置数据可携权可以先在一些试点性领域展开。比如,美国最先采取数据可携带权的试点是医疗领域,如果患者的医疗检查信息能够在医院之间实现迁移,那么对于医生准确判断患者病情以及未来应采取何种医疗措施是非常有益的。
“如何解决数据堡垒、数据垄断、数据不正当竞争,还是要回归数据本身,从数据的逻辑出发,在数据中寻找答案。”她说。
出品:南都反垄断研究课题组
采写:南都记者马嘉璐 见习记者孙朝